桑东辉 | 王夫之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以人性论、民本观、夷夏观为考察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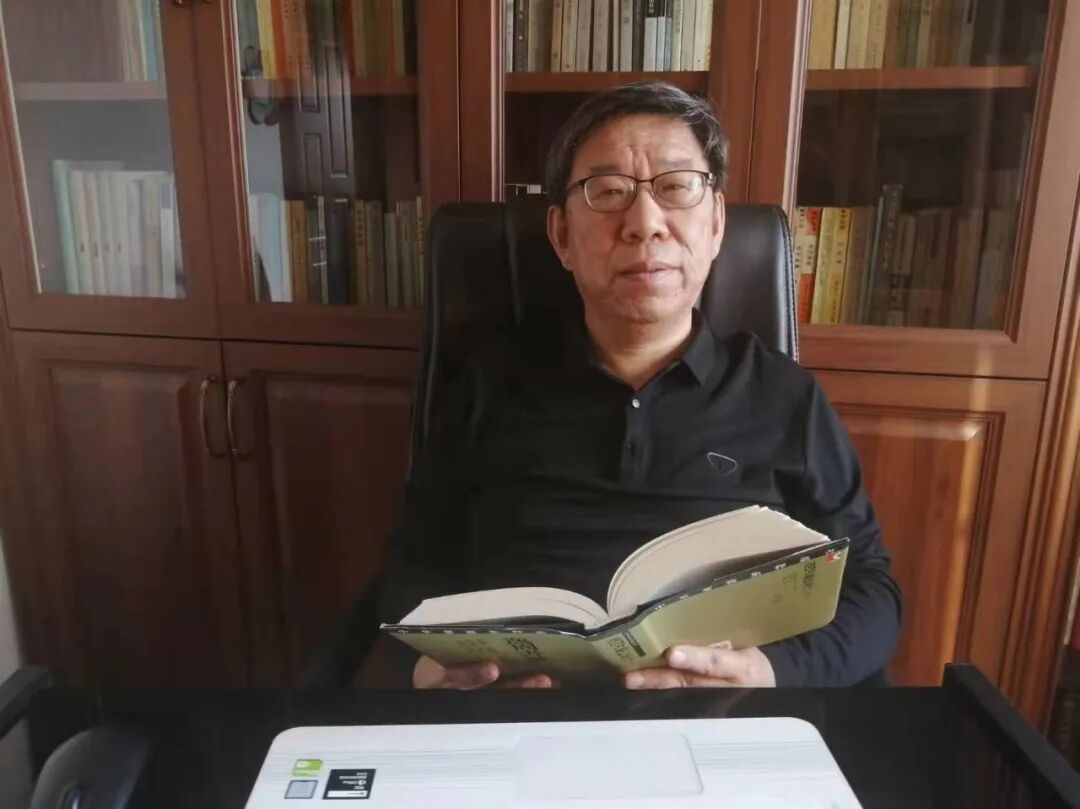
摘 要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战国时期的孟子和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是两大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巨擘。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面对的社会问题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孟子和王夫之都将其思想根基锚定在人性论这一人伦思想的基础上,并从人性论出发,针对君民关系、夷夏关系等国家治理的根本问题,提出了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主张。站在儒家学者立场,王夫之不仅吸纳、继承了先哲孟子人性论、民本观、夷夏观的思想精华,而且还对其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反映出中国古代启蒙思想的嬗变轨迹。
孟子思想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是具有启蒙意义的,其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明末清初启蒙思潮中的顾、黄、王都深受孟子的影响。其中,王夫之对孟子思想尤为重视。他不仅继承和吸纳了孟子性善的人性论、民贵君轻的民本观、用夏变夷的夷夏观等思想精华,还结合明末清初的社会现实,对孟子思想进行了批判继承和创新发展。本文主要从人性论、民本观、夷夏观的视角,探究孟子思想对王夫之的影响,以及王夫之对孟子思想做了哪些继承和发展。
一、从性善到性日生日成:王夫之对孟子人性论的继承与发展
在人性论问题上,孟子旗帜鲜明地主张人性本善,成为中国古代性善论的最典型代表。而王夫之的人性论则较为复杂,是在性善论基础上的一种动态人性论,即认为人性是“日生日成”的,将人的本性与后天环境影响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孟子人性论的核心内涵
孟子性善论的核心在于其对“四端之心”的阐述,并将“四端之心”看作是人性本善的发端,是人区别于禽兽的关键所在。孟子明确提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以恻隐之心而论,在孟子看来,“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这种恻隐之心是与生俱来的,也是非功利性的,体现了人对同类生命的关怀和爱护,是人性善良的最初和本能的表现。同样,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也都是人天生所具备的,并非后天产生的。在孟子看来,“四端之心”是人人皆有的,就如同人天生就有四肢一样自然。这是人性本善的直接体现,也是人类道德行为的内在根源。他强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即仁义礼智这些道德品质并非外部力量强加给人的,而是人内心本来就具有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天生就是完美的道德人,“四端之心”只是善的萌芽,还需要通过后天的培养和扩充,才能真正发展为完善的道德品质。只有通过教育、修养和实践,将“四端之心”扩而充之,才能使仁义礼智的道德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自觉尊奉的行为准则,从而实现个人的道德完善和社会的和谐有序。
要激发和扩充人性本善的“四端之心”,就要坚持“存心养性”的道德修养训练,以期通过后天的努力保持住并不断扩充人天生所具有的善端,来实现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关于这一点,《孟子·告子上》说得很清楚,所谓“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在这里,孟子将人的仁义之心比喻成山上的树木,因为外界环境的破坏而丧失了本性的美善。在孟子看来,要想保持和发扬人原初本性的善端,就要“存心”,即保持良善之心,使之不受外界干扰和侵蚀,所谓“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在“存心”的同时,还要“养性”,即培养人的性情和气质,使其符合道德标准。孟子认为,人性中的善端需要通过不断的修养和扩充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所谓“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关于孟子人性论的形上依据,学者们多将其归结为天道,认为孟子是“以天论德”,因天论性,即从天的角度来看待人性根源。如有的学者在论及孟子所谓的人人皆具良善本心时,指出:“孟子沿用先前天论的思想传统,把这个复杂的问题推给了天,公然宣称,这一切的一切,其终极的原因全在于天。”还有的学者认为,孟子以性善作为道德与天命的中介环节,是一种天赋道德论。孟子的性善论无疑是天赋的,并成为其“政治思想和伦理学说的理论基础”。概言之,孟子关于五伦、义利、民本等思想理论都来自其性善的人性论,他的仁政观念更奠基于人性皆善的基础之上,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可以说,孟子的人性论是其伦理思想的基础,是打通天道与人类社会治理之间的重要环节。
(二)王夫之人性论的核心思想
孟子不仅是性善论的肇始者,也是中国传统气论的开创者。在孟子看来,存心养性的重要修养方法是养气,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这个“气”是“集义所生”(《孟子·公孙丑上》),是使先天的性善转化为后天道德践履的关键。尽管孟子在人性与气之间凿开了一条进路,但真正将气与人性联系在一起并作深入阐发的则是其后世的学者,如王充、张载、王夫之等。王夫之深受孟子和张横渠的气论思想影响,将气的理论应用于人性论的建构中,提出“性者生理”且“日生日成”这一具有“气本论”色彩的人性论。
在《尚书引义》中,王夫之指出:“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在他看来,人性是人生命中所包含的社会道德属性,其基础是气,因为人是由阴阳五行之气所生,而理又寓于气中,其凝而成为性。简言之,“天以其阴阳五行之气生人,理即寓焉而凝之为性。故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莫非理之所宜”。王夫之认为,人性中的理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气紧密相连。同时,人性包含了人的社会道德属性,如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这些是人区别于其他生命体的重要特征。它们指导着人的行为,使人能够遵循道德规范,展现出善良、正义、谦逊等品质。在这一点上,王夫之继承了孟子将天命、人性、气之间紧密联系的理论预设,也“把宇宙论、本体论直接引以为人性论确立的依据。他从‘天命之谓性’立论,以‘天以理授气于人,此谓之命’为宇宙论、本体论向人性论的转折理论”。
王夫之的“性者生理”观点与他的“气本论”密切相关。在王夫之的世界观中,“气”是世界的本源,是万物之母,所谓“太虚即气,絪缊之本体,阴阳合于太和。……太虚者,阴阳之藏,健顺之德存焉;气化者,一阴一阳,动静之几,品汇之节具焉”。在王夫之看来,“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凡虚空皆气也”,“天地之产,皆精微茂美之气所成”。同理,人也是气化所成的,所谓“人之生也,气以成形,形以载气”。进而,人性也是气化流行的产物,即“夫人之有形,则气为之‘衷’矣。人之有气,则性为之‘衷’矣”。他明确指出:“气之化而人生焉,人生而性成焉。由气化而后理之实著,则道之名亦因以立。是理唯可以言性,而不可加诸天也,审矣。就气化之流行于天壤,各有其当然者,曰道。就气化之成于人身,实有其当然者,则曰性。”在此,王夫之清晰地阐述了人性源于气化的整个过程,即气的运动变化产生了人,而人性则在人的生成过程中得以形成。气的运行和变化是自然而然的,没有外力的强制,这体现了王夫之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对世界本质的深刻理解。
王夫之对人性论的贡献在于,他虽然没有超越“天命之谓性”的传统思维模式,但他将传统哲学的理气说与性理说结合起来,认为“性只是理”,“性,理也”。而理又在气中,所谓“气者,理之依也”。故而,“性在气中”。在王夫之看来,人性主要就是气质之性,他反对宋儒将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割裂开来的二元论,主张“理气合一”的一元人性论。
王夫之将气与人性紧密结合,并将气的运动变化应用到人性理论中,生发出“日生日成”的动态人性论。与形而上、一成不变的静态人性论不同,王夫之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人性,认为人性是随着外界环境不断变化而变化的,即人性是动态变化的,因“习与性成”而“日生日成”。在《尚书引义》中,王夫之指出:“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也。”在他看来,人的行为习惯一旦养成,就会对人性产生深刻影响,人性也会随着习惯的养成而发生变化。这种人性论强调的是后天习染对人性形成和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突出了人性在后天的学习和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朱贻庭先生认为:“王夫之论人性的主要特点和杰出贡献,在于他提出了‘性日生则日成’和‘习成而性与成’相统一的人性形成过程论。”
概言之,王夫之的人性论认为人性作为人区别于其他生命体的根本特质,是在气的运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种基于气本论的人性论,打破了对人性的神秘化解释,为人们理解人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为中国古代人性论史增加了新的内容。
(三)王夫之对孟子人性论的继承与发展
孟子的性善论与王夫之的“日生日成”人性论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人性论史上思想传承与创新的典型例证。王夫之作为明末清初的儒学大家,在继承孟子性善论核心精神的基础上,结合宋明理学与自身体悟,提出了更具动态性和实践性的人性论。
在人性论问题上,孟子主张人性本具“四端之心”(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认为善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王夫之继承了人性向善的根本方向,强调“性者,生之理也”,即人性中蕴含向善的生机与潜能。他肯定人性中具有道德自觉的可能性,这与孟子性善论的精神内核一致。
在道德主体的自觉性问题上,孟子强调“尽心知性”“存心养性”,主张通过道德实践来发显善性。王夫之同样重视主体的道德实践,提出“性日生日成”思想,认为人性在动态的修养中不断生成和完善,进一步发展了孟子重视主体能动性的思想传统。
尤为可贵的是,王夫之在继承孟子性善论基础上,不仅提出“习与性成”的理论,还生发出“性日生日成”的动态人性观。按照王夫之“未成可成,已成可革”的观点,人性并非先天固定、一成不变,而是在生命历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外部环境的改变以及个人习性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这既保留了孟子人性向善的总基调,又突破了其静态性,将人性论纳入时间性与历史性的维度,实现了对孟子以降性善论的哲学重构。孟子性善论常被后人简化为“人性本善”的静态命题,而王夫之则通过“气本论”哲学,提出“性者,生之理,未死以前皆生也”,将人性看作是受“气化”与“习成”共同影响的动态过程。他批评宋儒将人性割裂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元论,主张人性是“理气合一”的产物,强调“习与性成”,即后天实践对善性具有塑造作用。“过去都是把生来固有的本性称为性,而他认为先天的是性,后天的也是性。孟子将先天之性称为‘端’,陈确把修养成性叫做‘全’,而王夫之把从端到全的过程叫做性的生成过程,也不无道理。”
在道德修养论方面,孟子强调道德实践,但偏重内在的心性修养。王夫之则将人性论与经世致用相结合,提出“行可兼知”,主张通过“践形尽性”的外在实践(如礼乐制度、社会活动)来实现人性的完善。这一转向使性善论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由人性引发的“情”与“欲”的问题,孟子是以“寡欲”为修养路径的,而王夫之则充分肯定人的合理欲望的正当性,提出“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将基本人欲纳入人性善的实践框架,避免了对人性的禁欲主义解读。
概言之,王夫之的人性论在继承孟子性善论的基础上,站在气本论哲学的高度,从历史实践的视角,实现了对传统人性论的创造性转化。该理论既回应了明末理学日益僵化的问题,也为清代实学思潮开辟了进路。
二、从民贵君轻到公天下:王夫之对孟子民本观的继承与发展
如果说提倡性善的人性论是孟子思想的基本内核,那么,主张“民贵君轻”的民本观就是孟子思想的合理内核。王夫之不仅极大地继承、创新、发展了孟子的人性论,而且对孟子的民本思想也全盘接受,并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围绕君臣民三者关系,提出了他的一套民本论,而其中核心内容又涉及“公天下”的天下观以及国家观和君臣观、人民观等。
(一)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内涵
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是“民贵君轻”。在《孟子·尽心下》中,孟子明确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观点将民众的地位置于国家和君主之上,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政治观念。在孟子所处的时代,君权至上的观念根深蒂固,但他却敏锐地洞察到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国家的根基在于民众,君主的统治必须以民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君主才能稳固地统治国家;若失去民心,君主的统治必将岌岌可危。
孟子以桀、纣失天下的历史教训为例,深刻阐述了民心向背决定政治成败的道理。桀和纣作为君主,在执政期间施行暴政,不顾民众的死活,肆意压榨剥削百姓,导致民不聊生。他们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民众的意愿,使得民心尽失。最终,在民众的反抗和反对势力的讨伐下,桀、纣都失去了天下,成为历史上暴君的代名词。正如孟子在《孟子·离娄上》中所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在梁启超看来,孟子对于专制君主的抨击“不惟责备君主专制之政而已。今世欧美之中产阶级专制,劳农阶级专制,由孟子视之,皆所谓‘杀人以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者也”。
与性善论一样,孟子的民本观也与其仁政思想紧密相关,如果说性善论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基础,民本观则是其仁政思想的重要实践路径。具体而言,民本观涵盖了养民和教民两个关键层面。
在养民层面,孟子提出“制民之产”的主张。他认为民众拥有稳定的产业是生活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孟子·梁惠王上》)所以,明君应“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具体说来,就是要为民众提供足够的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如“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通过合理的土地分配和生产资料扶持,让民众能够自给自足,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
作为民本思想的治理实践,仁政还体现在使民以时、不耽误民众生产活动的悯农恤民方面。“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只有保证民众有足够的时间从事生产活动,才能实现粮食的丰收和资源的可持续供给,使民众生活富足,安居乐业。
仁政不仅要爱民如子,更要轻徭薄赋。孟子反对统治者对民众进行过度盘剥,主张减轻赋税,让民众能够休养生息。他批评“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上》)的社会现象,认为这是“率兽而食人”的暴政,统治者应减轻民众的负担,让民众能够享受劳动成果。
在教民层面,孟子同样给予了高度重视。他认为“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通过兴办学校,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宣扬孝悌等伦理观念,使民众知晓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关系和应尽的义务,从而培养起良好的道德风尚,构建起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当民众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懂得了孝悌之义,就会在日常生活中尊敬长辈、关爱他人,社会上就会出现“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的道德盛世景象。这种道德教化不仅有助于提升民众的个人素质,还能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基础。
尽管孟子极力宣扬仁政爱民和民贵君轻等民本主张,但从思想本质上讲,萧公权认为“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简言之,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观念”。孟子思想中的民是没有民权的,即孟子关于民的思想是民本而非民主。对于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民本本质以及其“与民主的思想尚隔一间”的说法,徐复观也从原本赞同转而详思萧公权关于民享、民有、民治的讨论,认为对孟子的“民”思想需辩证地深入地分析。在徐复观看来,民治的制度固然实为孟子所未闻,但民治的原则,在《孟子》中已可看出端绪。不管怎样,孟子关于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不仅在其所处的战国时期是一种大胆的理论创新,而且对于中国古代思想界也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二)王夫之民本思想的核心内涵
王夫之在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对“理气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创新,并将其与孟子的民本思想紧密结合,从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高度更加深入地论证了民本思想,将民本思想延伸到天下、国家以及君臣民的关系等讨论中。
王夫之将“理气论”应用到民本思想中,认为民众是构成社会的基本物质实体,就如同“气”是构成世界的基础一样。民众的生存和发展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统治者的治理活动必须以民众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为依据,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即“理”。王夫之从“理气论”的角度出发,进而提出“理势合一”“理依于势”的人类社会进化史观,并以此作为理论根基,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其民本思想。
如前所述,在王夫之看来,“凡虚空,皆气也”,所谓“气者,理之依也”,而历史发展也是在“理”的指导下遵循一定趋势和规律运行的。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民众是不可忽视的,也是君王统治的重要基础。在这种历史观指导下,王夫之进一步完善了其民本思想,认为统治者的权力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源于天道,而天道的根本又在于“佑民”。就像“理依于气”一样,君主的统治也离不开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这种将“理气论”与民本思想相结合的观点,使王夫之的民本思想更加具有哲学高度和理论深度,从根本上论证了民本思想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王夫之构建了明辨君臣民三者关系的民本思想。在他看来,首先,君以民为基。他深刻认识到君主与民众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依存关系,明确提出“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的观点。其次,臣也要为民行德政。王夫之主张臣子乃“君之心膂、国之桢干、民之荫借者”,其不仅要忠于社稷,还要效忠君王,更要为民服务。臣子作为君主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和媒介,应时刻关注民众的切身利益,积极为民众谋福祉,而不是只考虑个人的安危荣辱,所谓“大臣之道,不可则止,非徒以保身为哲”。再次,统治者应满足人民的基本物质需要。王夫之从哲学的高度深入论证了民众物质需求的合理性,认为人的物质欲望是与生俱来的,是天理的自然体现,不应被压抑和否定,所谓“有欲斯有理”,人的欲望是天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所谓“饥则食,寒则衣,天也。食各有所甘,衣亦各有所好,人也”,人的基本欲望并非违背天理,而是天理在人身上的具体体现。“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最后,提出“宽以养民”的政策主张。在赋税方面,王夫之主张“减赋而轻之”;在徭役方面,王夫之主张“节役而逸之”;在土地制度方面,王夫之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但他对土地兼并问题表示了深切的关注,认为土地不是王者的私有财产,不应该被少数人垄断。他主张限制土地兼并,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总的说来,一方面,王夫之主张统治者要尊奉天道,顺应民心,关爱百姓,实施仁政,因为这是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圣人之大宝曰位,非但承天以理民之谓也,天下之民,非恃此而无以生,圣人之所甚贵者,民之生也,故曰大宝也。”另一方面,如果统治者倒行逆施,与民众为敌,就会失去民心,失去统治的合法性,最终导致政权的灭亡。南朝宋齐递嬗,“嗣是而掇天位者如拾坠叶,臣不以易主为惭,民不以改姓为异”。
王夫之的民本思想还体现在根据“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原则而提出的“公天下”政治思想上。他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君主是为了治理天下、保障民众的利益而设立的。他指出秦汉以后的帝王以天下为一姓之私产,统治者所制定的政治制度和政策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忽视了民众的利益。他提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君主应该遵循天理,以公心治理天下,摒弃个人的私欲和偏见,制定符合民众利益的政策。
(三)王夫之对孟子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王夫之的民本思想深深扎根于儒家思想的沃土之中,他继承了历代儒家特别是孟子的民本、仁政等思想,并结合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创新。
首先,王夫之将孟子“民贵君轻”思想推崇到天道等同于“民心之大同”的高度。王夫之在继承“民贵君轻”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天道佑民的理论预设,进一步深化了对民众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比如,同样是谈民本,孟子虽然也将民本的理论依据推之于天,但其停留在《尚书·泰誓》所谓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层面,而王夫之则进一步强调“天”就是“人之所同然”的“民心之大同”,所谓“民心之大同者,理在是,天即在是”。王夫之将历史过程中“不尽然”的民和民意转换成“不得不然”的天,以此来解读民本思想和天人无二,从而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推向了又一个认识的高点。这一认识也成为王夫之理想政治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王夫之进一步提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的观点,将民众的生死存亡视为高于一家一姓王朝的兴衰亡替,强调民众的利益才是国家的根本利益。这一观点突破了传统的君臣观念,体现了王夫之对民众主体地位的高度重视。他认为,国家的兴衰成败取决于民众的支持与否,取决于民心的向背,君主只有以民为本,关注民生,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若君主违背民意,施行暴政,甚至危及华夏民族命运,民众有权推翻其统治,即“可禅,可继,可革”。王夫之的这一观点与孟子“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的思想一脉相承。王夫之还通过对历史的分析,进一步阐述了“公天下”的内涵,并得出结论:政权的更迭应该以民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不是仅仅为了满足少数人的权力欲望。王夫之的“公天下”观念是对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在理论上更加深刻,在批判君主专制制度上更加有力。这一观念体现了王夫之对民众地位和作用的高度重视,以及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变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次,王夫之深化了对君臣民三者关系的再认识。在继承孟子民本思想的基础上,王夫之对君臣民关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和深入阐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本思想的内涵。孟子认为,君主应该以民为本,施行仁政,关心百姓的疾苦,得民心者得天下。王夫之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君主是为民众而设立的,其职责是保障民众的利益。此外,王夫之对臣子的职责也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臣子不仅要对君主尽忠,更要对民众负责。王夫之还强调了民众在君臣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君臣关系的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生活和国家的稳定。王夫之关于“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的观点进一步凸显了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他认为,尽管君主权力和地位的合法性来源于天道和天意,但民是国家的基础,是君主统治的对象。只有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君主才能稳固地统治国家。王夫之对君臣民关系的再认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对后世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最后,强化了对民众经济利益的重视。王夫之在经济思想上深受孟子的影响。他高度重视民众的经济利益和生活诉求,肯定民众追求经济利益的合理性和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正当性。王夫之继承了孟子“制民之产”的思想主张,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了人们物质需求的合理性。王夫之主张民众追求经济利益的欲望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所谓“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王夫之呼吁统治者要为民众从事生产活动创造条件,只有百姓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君王的统治才能稳固。
概言之,王夫之对孟子等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深入反思,在继承传统民本思想核心价值的同时,对其中一些不符合时代发展和社会现实的内容进行了修正,从而形成了具有独特内涵和时代特色的民本思想。
三、从用夏变夷到严华夷之防:王夫之对孟子夷夏观的继承与发展
夷夏问题是中国自古以来关心政治的思想家所不能规避的重大问题。孟子所处的东周列国时期已经出现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国家民族危机。到了王夫之的时代,更是面临清军入关的剧烈民族冲突。对于夷夏观,孟子和王夫之都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明确的表述,而且二者在夷夏观的问题上还有着某种思想上的传承和创新关系。
(一)孟子的夷夏观
孟子夷夏观的核心就是以礼义文化来区分夷与夏。在《孟子·滕文公上》中,孟子曾批评许行的追随者,所谓“今也南蛮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孟子以“南蛮鴂舌之人”称呼许行等人,强调他们来自南方,言语如同鸟语般难以理解,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学说不符合先王之道,即不符合华夏的礼义文化传统。孟子肯定的是陈良那样能够自觉学习华夏先进文化的人。虽然,陈良来自文化相对落后的楚国,但其“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孟子·滕文公上》)。在孟子看来,周公、仲尼之道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包含仁、义、礼、智等道德准则,以及一套完整的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遵循先王之道,就是遵循华夏的礼义文化,这是华夏民族的精神支柱和身份标识。与华夏的礼义文化相比,夷狄文化在孟子眼中存在诸多不足。夷狄的生活方式往往较为原始、粗放,缺乏华夏那种精细的社会分工和礼仪规范,更缺乏华夏文化那种系统完备的道德观念。在对待夷夏文化问题上,孟子明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
围绕夷夏关系问题,孟子的思想并没有停留在区分华夷标准上,而是提出采取“用夏变夷”的方式来影响落后的民族地区,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孟子认为,华夏文化具有先进性和优越性,应当主动地向周边民族地区辐射和传播,促使夷狄接受华夏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从而实现文化的交融与民族的融合。这一主张的理论基础源于孟子对华夏礼义文化的高度自信,他坚信华夏文化所蕴含的道德准则、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能够为夷狄地区带来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孟子对夷夏关系的认识并不是绝对对立和僵化不可改变的。孟子在强调华夏文化优越性的同时,认为夷夏之间并非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文化的差异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通过交流与学习来改变的。当夷狄接受华夏文化的熏陶,认同并遵循华夏的礼义规范时,他们就可以被视为华夏的一分子。《孟子·滕文公上》的文本“提供了来自两个方向的文化事实,即既有夷变夏,又有夏变夷。夏变夷的蹊跷在于夏并非一个实指的夏,而是一个文化意味、价值意味的夏。夷也并非一个实指的夷,而是一个文化与价值意味的夷”。在《孟子·滕文公上》中,孟子极力称赞楚国人陈良虽出身于被视为蛮夷的南方地区,但倾心于周公、仲尼之道,不远千里来到中原学习华夏文化,其勤奋和专注程度甚至超过了北方的学者。陈良的行为表明,夷狄之人可以通过对华夏文化的学习和对儒家伦理的认同,实现从夷到夏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个人身份的转变,更是一种文化认同,体现了孟子对夷夏关系动态发展的认识。
(二)王夫之的夷夏观
王夫之认为:“夷狄之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篾不异焉。乃于其中亦自有其贵贱焉,特地界分、天气殊,而不可乱;乱则人极毁,华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于早,所以定人极而保人之生,因乎天也。”在他看来,夷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这种差别首先源于自然环境的不同,进而导致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价值观念等文化层面的巨大差异。比如,在风俗习惯方面,华夏民族较之于少数民族更注重礼仪,有着一套繁琐而严格的礼仪制度。这套礼仪制度涵盖了祭祀、婚姻、丧葬、社交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了华夏民族对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的重视。在价值观念上,华夏民族受儒家思想影响至深,形成了以“三纲五常”为主的核心价值体系和以“忠孝节义”为主的核心价值观,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而夷狄的价值观念则更多地受到其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的影响,他们更加强调力量、勇气和生存能力。王夫之通过对夷夏在自然环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差异的分析,系统阐述了华夷有别的观点。王夫之认为礼仪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体现了文明与野蛮的分野,所谓“禽兽不能全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文之不备,渐至于无文,则前无与识,后无与传,是非无恒,取舍无据,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植立之兽而已”。这种观点为他进一步探讨夷夏关系和民族文化问题奠定了基础。
在王夫之的思想体系中,“夷夏观”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对其政治思想和文化观念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从政治思想层面来看,王夫之认为,“夷夏观”对政权合法性的判定和民族国家的构建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他看来,华夏政权的合法性源自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历史传承。华夏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道德伦理、礼仪制度和政治理念。王夫之坚信这种文化的优越性使得华夏政权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正统性。相比之下,夷狄政权本身则不具有正统性,而且有义务接受华夏文化的影响和改造,实现“用夏变夷”。此外,王夫之的“夷夏观”强调以华夏为核心,凝聚民族力量,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从文化观念层面来看,王夫之认为华夏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只有通过传承和弘扬华夏文化,才能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他看来,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不仅要有共同的习俗,更要有普遍认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王夫之主张通过文化传播等方式,将华夏文化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从华夏文化圈的核心辐射传递给周边地区,使周边民族地区在文化上形成对华夏文化的高度认同和归属。比如,在王夫之看来,文明与野蛮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客观地指出:“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他还以南方社会发展为例,指出:“吴、楚、闽、越,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在王夫之看来,所有的民族国家都是从野蛮走过来的,不仅中原地区远古是野蛮的,而且吴、楚、闽、越在汉代以前也是落后野蛮地区,经过千余年的发展,才变成了“文教之薮”。
王夫之的夷夏观最终落脚点为“严华夷之大防”这一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倾向上。虽然这种思想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和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王夫之生活在明清易代的特殊历史时期,面对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剧烈的民族冲突,他极其重视“华夷之大防”,强调华夏文化的正统性,全力维护华夏文化和华夏民族的传承。他主张对夷狄要保持警惕,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抵御夷狄,防止其对华夏文化的冲击。在这一点上,王夫之思想是有其狭隘性的。比如,王夫之主张华夏与夷狄之间应该“各生其所生,养其所养,君长其君长,部落其部落,彼无我侵,我无彼虞,各安其纪而不相渎耳”。对于不能坚守这一夷夏邦交原则甚至“逾防而为中夏之祸”的少数民族,王夫之主张坚决抗击且不必考虑仁义、诚信等道德问题。他反复重申,对于给华夏造成威胁的夷狄,“殄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掩之而不为不信”,“欺之而不为不信,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者也”。尽管王夫之的这些言论主要是一种极端化情绪的宣泄,但“对于一个热爱祖国、却又正处在异族入侵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家来说,夷夏问题就显然不仅仅是个学术话题,而是一个必须倾注爱与憎的情感焦点;因此夫之在论述中不能不有过激之言词,其思想也难免有理性与情感的冲突与矛盾。这是在理解夫之夷夏观时所应注意的”。
(三)王夫之对孟子夷夏观的继承与发展
孟子以道德来区分人禽、以文化来区分夷夏的思维模式对王夫之以道德和文化评判夷夏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孟子以“四端”之心来区分人禽的主张,王夫之是认同的,他也用道德和文化来区分夷夏,认为华夏民族之所以优于夷狄,不仅仅在于地域、种族等外在因素,更重要的是华夏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备的道德伦理体系(即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十分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道德秩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仁而已矣。中国之所以异于夷狄,仁而已矣。君子之所以异于小人,仁而已矣。而禽狄之微明,小人之夜气,仁未尝不存焉;惟其无礼也,故虽有存焉者而不能显,虽有显焉者而无所藏。故子曰:‘复礼为仁。’大哉礼乎!天道之所藏而人道之所显也。”在王夫之看来,夷狄往往缺乏这种深厚的道德文化底蕴,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与华夏民族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在《读通鉴论》中,王夫之对历史上一些夷狄政权的暴虐行为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不懂得仁义道德,往往表现得残忍、野蛮和落后。这种以道德和文化区分夷夏的思维模式,使王夫之更加注重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他认为,华夏民族的道德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支柱,只有坚守和弘扬这种道德文化,才能保持华夏民族的独立性和优越性。
王夫之的夷夏观深受孟子的影响,在政治理念上突出表现为对攘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他对历史上的夷夏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强调夷夏之间的界限和区别,认为华夏民族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中心性和完整性,加强对周边夷狄民族的防御。针对孟子颂赞“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孟子·滕文公下》),王夫之慨叹道:“此一片中原干净土,天生此一类衣冠剑配之人,如何容得者般气味来熏染?”并积极主张对夷狄采取“兼之驱之”的措施加以“廓清”。在王夫之看来,只要华夏子孙团结一心,“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族类强植,仁勇竞命,虽历百世而弱丧之祸消也”。
王夫之对孟子“用夏变夷”思想亦持有高度认同的态度。在王夫之看来,“遐荒之地,有可收为冠带之伦,则以广天地之德而立人极也”。也就是说,在周边民族文明程度提高后,中原政权可以将华夏文明覆盖到民族地区,所谓“君臣父子之伦,诗书礼乐之化,圣人岂不欲普天率土而沐浴之乎?时之未至,不能先焉”。王夫之以人伦秩序构建夷夏关系的认知,为理解夷夏之间的政治、文化和道德关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这种思想不仅反映了他对华夏文化的自信和对夷夏秩序的维护,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对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态度。
王夫之的“夷夏观”进一步强调了华夏文化在文化传播中的主导地位,所谓“内中夏,外戎狄”。他认为,华夏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精华,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体现在各个方面。尤其在道德伦理方面,华夏民族构建起了一套完备的道德体系,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和思想。王夫之继承了孟子的文化传承精神,将保护和传承华夏文化视为自己的神圣使命。“故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强干自辅,所以凝黄中以絪缊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地仁义之云云也哉!”王夫之认为,华夏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必须加以传承和弘扬。
如果说孟子的夷夏观还只是一种华夏中心论和文化优越论,那么,王夫之的夷夏观在某些方面一定程度走到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道路上。其主要表现在过度强调华夏民族的优越性,将华夏民族视为道德、文化和政治的绝对中心,而将夷狄民族一律视为落后、野蛮的存在。王夫之对夷狄的评价往往带有偏见,他认为夷狄“不知礼义”“贪暴无厌”,其行为与禽兽无异。王夫之主张“嘉禾不与燕麦同陇,仁禽不与妖鸟同巢。辨其异,慎其同,大统以正,大义以明,从其类而不可乱”。这种极端的言论充分反映他对夷狄文化的排斥和否定态度。他认为夷狄文化缺乏道德伦理和文明礼仪,与华夏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使得夷狄文化无法与华夏文化相提并论。尽管王夫之的夷夏观具有一定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其当时处于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严峻形势下,其根本立场和出发点主要是为了反抗来自满人的民族压迫。除此之外,王夫之还是主张华夏民族与塞外少数民族和平共处的。
四、结 语
王夫之虽然与孟子相距两千年之久,但他们都处在一个新旧交替、民族冲突的大变革时代。他们就像思想上的隔世知音一样,都提出了对中国历史影响至深的启蒙思想。在关注的问题域上,王夫之和孟子都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焦点聚焦在人性论、民本观、夷夏观等方面。比较而言,孟子的思想是具有开创意义的。比如,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系统地提出了人性善的性善论,第一个大胆地阐发了“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在夷夏观方面,孟子提出了用夏变夷的主张。在中国启蒙思潮中,王夫之的思想也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明清嬗代之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冲突,王夫之继承发展了孟子的思想。他将孟子的性善论发展为“日生日成”的动态人性论。在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基础上,王夫之提出了“天下非一姓之私”的“公天下”思想。围绕民族冲突,王夫之在孟子夷夏之辨和用夏变夷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严华夷之大防”的思想主张。尽管无论是孟子还是王夫之都没有完全超越自身的时代和阶级局限,他们的思想不乏保守落后的内容,但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孟子和王夫之对中国的思想界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思想启蒙作用。剔除其中腐朽落后的内容,孟子和王夫之围绕人性论、民本观、夷夏观的很多论述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作者:桑东辉,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客座教授